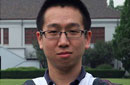原南昌大学校长:院士退休与否不能搞一刀切
 潘际銮院士资料图。
潘际銮院士资料图。
 潘际銮院士工作照片。
潘际銮院士工作照片。
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
潘际銮院士86岁了,但“退休”仍然是件很遥远的事情。
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,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,裹着灰色呢子大衣,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,“呼呼”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。
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,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,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。这座三层老建筑物的楼龄比这位院士还要小28岁,建于1955年。那时,潘际銮在这里筹建清华大学焊接专业。
在这座老焊接馆,“潘际銮”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,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。不过,对很多普通公众说,这个难读的名字,同样也很陌生。
与潘际銮相关的很多成就,已经被写进教科书。比如,中学生在地理课本里读到的秦山核电站,他是这项工程的焊接顾问。
很多人不知道,当他们乘坐着高铁,奔驰在铁轨上时,已和那位在焊接馆摸钢板的老院士,产生微妙的关联。潘老先生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,穿着厚棉袄,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,在深夜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。这年,潘院士已经年过80岁了。
不过,对这位“身陷”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,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“老”了的唯一指标。
比他小好几轮的同事郑军说,“潘老师还很年轻呢”。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,玩微信、看微博,家中电脑QQ“噔噔”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。
尽管已过耄耋之年,他可以不借助眼镜,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。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,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。当然,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、直径以及气压值。
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,摊开双手,自信地说:“我现在研究的课题,是焊接领域的前沿,比如“高超超临界”,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。”
尽管,潘际銮丝毫不认为自己的研究“过时”了,但是他用坦然的语气说:“我是一个老派的过时的科学家。”
如同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家,潘际銮喜欢回忆往事。他时常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,一边夹着菜,一边念叨起他的西南联大。
毕业50多年的老校友潘际銮,如今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。他说,自己之所以被选为会长,是因为“还很年轻”。这个中国著名校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,已经超过90岁。
如今,年纪越往上攀登,潘际銮的记忆,就越爱寻找属于西南联大的“焊接点”。
去年11月3日,在“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”上,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,聚在一起。他们有的被家属扶着,还有的已经“糊里糊涂了”。
当时,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,颤颤巍巍地站着,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。他们唱到“多难殷忧新国运,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复神京,还燕碣”时,潘际銮的心里“激动不已”。他环顾四周,看到眼泪顺着很多张布满沟壑的脸,往下淌着。
潘际銮说,他这么大岁数,还想“干活”,是因为自己“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”,仍然“可以为国家做贡献”。
“爱国”从这位老科学家的口里说出来,在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的耳朵里听着,“一点儿都不空洞”。
20多岁时,在炮火声中从老家九江逃难到昆明的潘际銮,“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”。
此刻,正当潘际銮坐在老旧的焊接馆里,“焊接”着往日的艰难岁月时,窗外晃动着很多年轻的身影。这一天,是2014年公务员“国考”日。
每一代青年人,都面临着人生选择。当年潘际銮主动报考焊接专业时,这门学科还很冷清。当时还有人笑话他:学焊接?学焊洋铁壶、修自行车干吗?
显然,当潘际銮决定学焊接时,并不能预见是否有光明的个人前途。不过,他认为,“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”。
这个西南联大44级校友说,“那时候读书,纯粹求学问,不想功名和前途。”
在他看来,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,是件“后知后觉”的事情。他回忆,当时“填了一张表”,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,而且“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”。后来,他被告知,“评上院士了”。
“我所获得的荣誉,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。”潘际銮说。
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,“对名和利,不敏感”。
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后,能让他惦念的事情,已经不多。1992年,他开始作为南昌大学校长的试验。10年间,他一直试图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和方式,“焊接”到南昌大学上去。
很多人眼里性格随和的潘校长,显现出改革者“铁腕”一面。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,实行“学分制”、“淘汰制”和“滚动竞争制”。
初入南昌大学,潘际銮晚上在校园里外散步时,经常看到学生在跳交谊舞和打桌球。这些场景显然与他记忆中的大学生活,并不相符合。
他总是回忆起,当年宿舍太拥挤,学生就去学校附近的茶馆看书和写论文。经常说起的例子是,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,在“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”小说。
潘际銮要扭转南昌大学的学风。“三制”的焊接轨迹,带有明显的西南联大特征。他并不讳言,自己大一时也曾物理考试不及格,而西南联大“8000多学生,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”。
作为南昌大学的校长,潘际銮“抓教学和科研”,但他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。
“他是个放权的校长。”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。
显然,这位老校长很了解,“管钱和管人,哪怕只是管分房子,都是很大的权力。”但是,他不亲近这些权力。
潘际銮用西南联大式的方法,重新拼接南昌大学。最明显的成果是,昔日薄弱的院校,在他任上的第五年,成为一所国家“211”重点大学。
不过,潘际銮的一些学生和下属却说,他们并没有跟着校长“沾光”,也没有得到“实惠”。
说起自己的导师,在南昌大学任教的张华,有“苦水”要倒。身为校长的学生,张华没有“获得更多资源”。相反,潘际銮跟他说:“你就默默无闻地干,自己去争取课题,别指望在学校拿钱。”
而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,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,一直到他卸任,直至自己离校,职级都没有改变。
当时,作为校长秘书,徐丽萍都不敢印名片,“那么大年纪,还是科长,实在不好意思啊”。
而潘际銮本人,对名片上的头衔,并不在意。2002年,他从南昌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卸任,回到清华园的焊接馆。
“校长不是我的终身事业。科研,才是我一辈子扑在上面的事。”潘际銮说。
从75岁开始,他的身份是个“无官一身轻”的焊接专家。当然,他还是院士。但他认为,院士于他而言,只是一种荣誉,不是权力。
他没有行政头衔,也没有秘书。他带着一个平均年龄60岁的团队,在墙皮有些脱落的焊接馆里,研究世界上焊接领域的前沿问题。
时下,这位手机屏幕里会跳出微博新闻的老院士,知道人们正在讨论院士制度。
潘院士并不否认,“有个别单位在‘包装’院士”。他也不讳言,“个别院士成为给单位装点门面的花瓶。这是院士被‘异化’的现象”。
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焊接专家,把围绕院士以及科研界存在的问题,比作钢板上的“裂纹”。不过,早期就以“热裂纹”为研究方向的潘际銮,攻克过无数个技术难题,但很难说清这些暴露在社会肌体上的“裂纹”,“究竟该怎么解决”。
如果深入探究那道“裂纹”,潘际銮认为,人们之所以担忧院士的退休问题,是不喜欢院士们成为“学术资源的垄断者”,或者享受“特殊待遇”。
现在,潘际銮仍在焊接馆的一间光线不好的屋子里办公。资料堆到墙边,以至于部分书被挤到窗台上。他的褐色办公桌和矮茶几角,已经部分掉漆,裸出木头的原色。
而他在南昌大学当校长时,办公场景比这一幕还要“寒碜”。他挤在办公楼西南角那间12平方米的屋里,秘书徐丽萍只能在过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间办公室。
有人劝他:“潘校长,外国学者也要拜访您呢,换间大的办公室吧。”
但潘际銮坚决不换,还说“西南联大那会儿,比这条件差好多呢”。
至今,他唯一享有过的“配车”,是在当校长的时候。那是一辆留学生捐赠给学校的老旧尼桑车。他的司机总忍不住抱怨:“校长,换辆新车吧。”
那辆汽车终于没被换掉,“最后都快报废了”。潘院士的电动自行车倒是换了一辆。他80岁生日时,学生送给他这辆眼下正骑着的银灰色“坐骑”,代替之前那辆电池笨重而且总是坏掉的“老古董”。
提起院士是否应该像老电动车一样“退休”,性情温和的潘际銮会有些激动。他反对“用行政化的方式来处理高知识分子人才问题”。
“院士是否退休,不能搞一刀切。个人情况不一样。”潘院士打比方,“这就像找专家挂号,有人找我帮他们解决难题。要是我没用了,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”。
如果没有“老糊涂”,潘院士就想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,“呼呼”地穿梭在清华园的一年四季里。
(原标题: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)